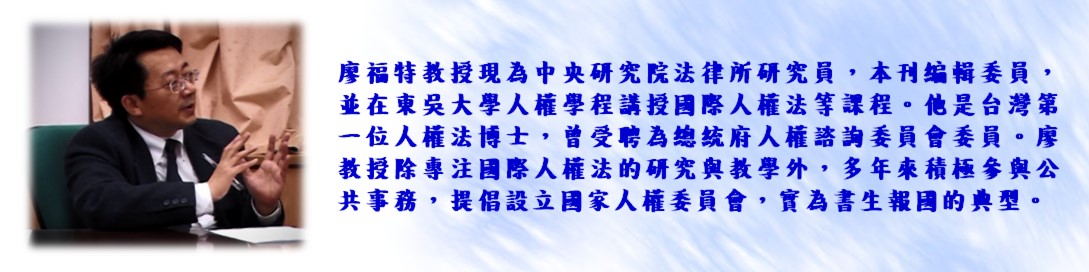
學術研究與公共服務|專訪廖福特||人權群像第一季第八集
廖福特
學術研究與公共服務:專訪廖福特教授
廖福特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研究員,本刊編輯委員,並在東吳大學人權學程講授國際人權法等課程。他是台灣第一位人權法博士,曾受聘為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委員。廖教授除專注於國際人權法的研究與教學外,多年來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提倡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實為書生報國的典型。
黃:大家好,我叫黃默,是東吳大學外雙溪人權研究中心的老師,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廖福特教授來做訪談。廖福特教授是我多年的老朋友,那這些年來他是從英國學成歸國以後,是在中央研究院,大部分時間是在中央研究院做研究,但是你再稍微進一步去觀察,不論在研究教學方面,還是參與政府、幫政府做諮詢的工作,多年來,從陳水扁政府到當前,為政府做諮詢的工作,或是參加民間的組織,廖福特教授都參與非常多,也做出非常多的貢獻。我們非常榮幸能邀請到他來接受我們的訪問,我想請他跟大家分享的,一方面是他的學術的生涯,這麼多年來他做的研究,那他是在Oxford,在華人當中是最早得到人權這一個專業的Ph.D的學者,那也在多年來,也都在東吳,在我們這裡的人權學程、人權碩士班兼課,對我們幫助非常多,不論是教學、不論是論文的指導。那同時他又參加,不論是為政府做這個顧問諮詢的工作,從陳水扁時代到當前。那我們就想請他分享,一方面是他的學術的生涯,另外一方面是他參與實際的人權的工作,人權的推動的、工作的經驗,廖教授,請。
廖:謝謝黃默老師,做一些介紹,那大概如果說可以去訴說幾個部份的話,第一個部份或許可以跟各位報告我個人的一些算近代史好了,幾個發展。那我個人對於人權的研究教學或是運動等等有興趣,應該我自己的感覺是從我在大學時候就慢慢開始培養起來。就是說,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是我在大學時候、大學二年級剛滿二十歲的時候,當時居然是很奇怪的在想一件事情:「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那當時在這些人權的法律方面的研究,對我來說開始有些興趣,不過剛開始我做的研究是比較偏向憲法的思考。就是也可能在當時那個年代有點關係,就是說我念大學的時候,台灣還在戒嚴的時代,法律來說的話,在公法學是剛剛開始去醞釀,希望能夠、台灣能夠走向民主化,以及人權的這些理念,我大學的時候其實對憲法很有興趣,我大二之後慢慢思考希望能夠去鑽研這些憲法的研究,特別是人權的部份。那後來不過就是,我自己有個因緣際會,就是在我當兵的時候到金門當兵,那時候金門兩年的時間又進入到一個戒嚴的狀態,我就非常的鬱悶,想說:「奇怪為什麼?不是剛解嚴嗎?」因為我大學畢業那年,剛好台灣解嚴的那年,可是我覺得跑到金門去戒嚴了兩年,那讓我在思索一些事情。那後來退伍回來以後,我回到台灣念研究所,就開始在思索還是對人權的法律有相當的興趣,不過後來就慢慢去想說我應該要在更進一步去問,是不是有一些國際人權的概念。所以我到研究所以後就慢慢開始去碰觸國際人權。不過大概當時台灣那個時代之下,國際人權在台灣其實是沒有什麼基礎的一個學科(黃:對,沒。),特別包括在法律系,也是沒有什麼老師教學的。以我當時那個狀態來看的話,就是開始在摸索的階段,那所以其實我後來在碩士論文就寫了一個歐洲人權公約一個訴訟的制度。那當時發現就是說居然有一個在你的國家訴訟窮盡國內救濟後,可以到國際人權法院去做國際人權訴訟這個制度,對當時那個年輕的我來說的話,幾乎是覺得不可想像,非常特別的一個制度,它就非常吸引我,把我比較引導到國際人權的這個方向去。那所以說我就後來慢慢開始去思考,我能夠做的研究的工作就是把國內的一些憲法公法學的概念跟國際人權做一些連結起來,就連結起來。那後來我就到英國牛津大學唸書,我就還是持續的去做歐洲人權法院的一些判決的研究。當時我的博士論文其實最主要是在有關於現在所稱的言論自由或表意自由,去做進一步的研究。那能夠到英國牛津大學唸書,第一個當然是我自己主觀的期待啦,我希望到歐洲繼續做歐洲人權公約的研究,另一個也是我幸運啦,就是可能因為大概台灣人到那邊念國際人權應該沒有什麼人啦,所以我就蠻幸運的,當時有指導老師願意就是讓我做這樣的工作,後來也順利的拿到學位,所以說我就開始我自己所埋下的、在那個國內的公法學跟國際人權交接、互動的這個研究的方向。
黃:我能不能插嘴一句,這我也想起來,在美國也是這樣情況。研究憲法的也都兼研究國際人權法(廖:對對對。),這在他們是一個視以為常的事情。但在我們國內,研究憲法跟研究國際人權法看來是有一個分野,好幾位研究憲法的都不怎麼願意去探討國際人權法,同時,比如說我想你也很瞭解,我們都經過這樣的一個情況,就好些研究憲法的都不怎麼同意說我們應該設一個國家人權委員會,這個跟國外情況有些不一樣的,你怎麼看?
廖: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台灣哦,我開玩笑,國際人權法是兩邊的孤兒。就是公法學者他比較著重於公法學,或者是比較憲法,他們比較著重研究比方說德國、美國、日本的憲法這種比較的概念,跟台灣這個情況⋯⋯另一個孤兒就是國際法,國際法他可能我就研究國際組織法、國際海洋法等等的法律,可是也沒相對去做比較專精的人權法研究,當然也就更沒有把兩者結合起來的研究了。那我覺得這是當時在台灣在這種歷史背景的情況之下,第一個公法學也是比較近期解嚴之後慢慢的發展;第二個國際法我們到目前為止其實也並不是發展得那麼完整,所以說比較難把這兩者把它連結起來,作為學術研究的一個主題。不過我是覺得台灣慢慢開始有這個方面的發展。那對我來說的話,我1999年拿到博士學位回到台灣嘛,那除了短暫一年在東海專任法律系專任之外,就很快到中研院,接下來十幾年的工作。那所以說我的研究,剛開始因為我在中研院是在歐美所,所以說我在那幾年的時間裡面,比較做深入的歐洲的人權方面的研究。那後來我轉到法律所以後,我就開始轉移到聯合國這邊,特別是兩個人權公約或是禁止酷刑公約,做反種族歧視公約,這些比較偏向、我偏向的題目還是比較一般我們所俗稱的公民政治權利啦,經濟社會文化權的部份相對而言是比較少。那另一個主題的話,就是特別是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這些主題的研究,那再過來一個主題就是怎麼把國際人權條約國內法化,這些是在我學術工作的、很快的就十幾年就花掉了,就在這些幾個部份的那個學術的研究的部份,那當然希望就是說未來不會變節,繼續做這方面,我預估還是未來的學術研究方向應該還是不會變,會持續的在這個公法學跟國際人權法交接的過程持續的去做研究。
黃:你的專書論文已經非常多了,在國內是少見的,國內沒有哪幾位,用我的話來講,中生代的學者有你這樣豐碩的著作,那我瞭解你今後幾年看來還是會維持在這個領域,在做進一步的探討。比如說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設置,怎麼樣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國家人權委員會,這樣瞭解沒有錯吧?
廖:是、是,主要的方向其實是...我在猜應該是不會變化,因為我相信就是說在一個學科的專業的耕耘來看,它其實需要長時間,並不是說幾年時間...當然會做出一點成果啦,可是真正要把它當作一輩子的志業的話是不容易的事情,這個需要長時間的耕耘跟堅持。
黃:這個我非常很同意。
廖:因為已經是耕耘跟堅持都不一定會有成果。
黃:但是如果不耕耘...一定沒有....
廖:更不會有成果。應該我想會持續下去。
黃:我瞭解你得到中央研究院一個、這個、一個研究計畫的補助,就是研究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怎麼樣的一個設置、一個比較理想的...是不是這樣(廖:是是是),這個計劃看起來是一個多年的計畫。
廖:對,它是一個五年的計畫,那我希望這五年裡面作到幾個主要核心的議題。第一個我可能要去處理的說,因為有人可能會去質疑,我們為什麼需要國家人權委員會,那所以說我希望第一個主題是去辯論,就是說我們為什麼需要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剛才黃老師你也提到,比較特別的現象是說可能比較鑽研於憲法的學者,反而對於這個議題並不是那麼的積極。那我可能覺得他是限於傳統的公法學論述,而沒有看到現在比較新的發展。所以我希望第一個主題去做這方面的辯論。那再過來它包括幾個主題,比如說第二個主題是我們在組織上的辯論;第三個主題是說在職權上的辯論;然後再過來第四個就必須把組織跟職權辯論交叉在一起,比方說在國家的制度上它怎麼結合,那第五個主題當然可能就考慮到整個國家人權委員會跟其他機關它的互動這個辯論的可能性,那是希望說在這幾個主題去探討。那另外的研究的方向比如說我另外有國科會的計畫,我是希望延續我博士論文在某一小塊再抽出來,我希望去處理一些仇恨、仇視言論,這個言論的概念的話,它在國際人權法的發展,以及它怎麼面對到國家如果要把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之後,這個議題要怎麼去安排跟處理。這大概是我兩個主軸的思考,那當然還有時間、還可以的話,我現在會比較關心的是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這個部份,相對而言它在國際人權法,也相對而言是比較新的,那對台灣當然也是一個新的議題(黃:對,是一個挑戰),對,那如果我時間允許的話...因為這個已經想到非常多東西了。
黃:是是是...我常想你怎麼能做那麼多的事情呢?研究、寫文章、出專書...那你談一談你的教學的經驗,你在我們這裡兼課很多年,對我們幫助很大,你稍微談談你的教學的...
廖:我必須誠實的說,我比其他學者來說,教學經驗應該是比較差,因為畢竟在中央研究院,它是一個研究機構,我們可能比較花比較多時間去做研究,那教學的那個時數或是經驗來說的話,相對來說比較少。有時候真的兩者不是能夠完全的兼顧得非常好啦。所以說我在教學,我絕大部分扮演的角色是一個兼任老師的角色,那所以說我覺得那個重心點就不太一樣。那它的好處就是說我只要做一個兼任老師,在我所教導的那個學科裡面能夠專精、專業化就好了,那相對而言指導的學生數量也沒那麼多。
黃:但你也指導不少位我們的同學。
廖:對,我盡力而為。
黃:我的看是不在是專任兼任,就是說有好些專門做研究的,不怎麼喜歡這個...教學,但是我的瞭解,你喜歡教學而且你也...教學對你而言是一個愉悅的經驗,我這樣說對不對。
廖:對,不會說是...至少不會是不好的經驗,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前提,就是說我喜歡中研院的情況是因為我專職是在研究,那我的上課時數不多,這個我自己的感覺比較像是外國研究型大學,也就是說可能我一週只有四個小時上課時數,所以我可以比較精確地安排我的研究跟教學,不會說因為我上課時數太多,而導致說我在上課感覺是種負擔。
黃:這也是我們當前的一個弊病,在大學裡面。
廖:對,對我來說因為我在中研院,所以說這種狀況會相對而言是比較好的。那第二個當然因為我是一個兼任老師,我上課的類型會比較符合我自己的研究,就是我上課讀的科目的話,可能是我自己所研究的科目,它的合致與自信會比較高一點,那所以我就不需要說好像其實是花在準備上課的時間會是那麼的多。那第三個我是說,因為我上課時間少,所以相對而言你不會感覺那麼負擔那麼重,那或許相對比較可以享受所謂的教學相長。因為我十幾年來感覺其實上課真的還是有幫助,因為我要上課,那要思考某些東西,可能也是因為要安排要備課或是等等,也是幫自己作為一些啟發,我覺得有些思考反而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所啟發出來的。那當然也包括指導學生的論文,因為每一篇指導學生的論文,也可能不見得是我那麼熟悉的、或者是那麼完整了解的議題。那透過這種討論、思考,對我自己也覺得也是一個幫助啦。
黃:對,我也喜歡上課,我覺得上課對我也非常多的幫助。那談談你跟政府的關係,你幫政府做諮詢的工作,從呂秀蓮...陳水扁、呂秀蓮時代,那到當前,還有跟這個...民間團體的互動跟在民間團體擔任的位子,比如說你跟台權會關係是非常密切的,稍微這方面稍微談一談。
廖:這是有關於政府的部份,其實我自己說我是躬逢其盛,我剛才說1999年拿到學位回來,大家都知道2000年的時候我們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先生當選總統,那所以說1999年來,其實我跟黃默老師我們當時在籌劃就是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部份,然後再慢慢的開始。那因為就剛好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嘛,那後來陳水扁政府開始設立的總統府諮詢委員會以及行政院的人權諮詢小組,那我剛好在那個幾年的時間,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我應該是在2001~2006在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然後再來有三、四年的時間在行政院人權委員保障小組,這邊工作。那在這部份的話,其實它扮演的是一個諮詢,對政府諮詢的工作啦。那其實是有一些間接,不過我覺得它的好處是說當時在陳水扁政府的時代的時後,它的好處是,過去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部份,它可以做的工作,因為我們的政府部門從來沒想到說可以在它的政府機制裡面設立某些人權諮詢的機制。這是我覺得它的好處。不過結構上的話,它是有一些,說是人權諮詢委員會嘛,所以基本上它扮演的諮詢的角色。那你諮詢的成果,其實還是在於一些政治的運作過程,重點是在於總統或副總統、包括行政院長,對於諮詢你的諮詢意見看待的一個情況。那不過我覺得在扁政府時代的好處是說,因為陳水扁總統他有宣示人權立國這樣的政策,所以當時在總統府諮詢委員會的話,最主要是在他2000年第一次就職的那個架構底下,去做那些重要的事情。雖然後來有些事情並不是那麼順利,那比如說我們設國家人權委員會從當時開始,不管從民間團體,或是扁政府提倡,一直到現在可能都還在努力當中。那批准兩公約,也是扁政府那時候開始提倡,那當然後來2009年馬政府的時候有完成。包括說人權教育,或者是個別的議題等等這些。那我覺得當時在做這些工作的話,它對台灣社會比較正面的幫助是說去建構一個我們對人權的認知還有人權文化的基礎。也就是說政府它本身是可以做這些工作的,不然我們以前都認為說,政府其實可能只會扮演人權的侵犯者,而沒有可能去把人權變成是一個政府的核心價值之一,然後慢慢地實現。或許實踐上並不盡如人意,但至少可以變成政府一個核心價值,變成我們施政裡面主要價值之一。這是我覺得它相對而言是比較能夠做的事情。那在扁政府時代的話,我是比較有直接的這個諮詢工作;那後來馬政府的話,我是比較間接,因為我是沒有直接在裡面,那我比較參與的部份是在可能兩公約的法案審查或是人權報告之類的部份,比較間接的那些...
黃:你現在還是那個國家人權機構...研究小組的顧問。你比較馬政府跟扁政府,你會做怎樣的一個評價?
廖:呃...我覺得以這個概念來看的話,扁政府其實它扮演的是一個火車頭的角色,在人權議題的時候,從沒有到開始去提倡,所以我覺得這是它正面的部份。相對而言可能面臨的問題是可能是沒經驗,因為過去的政府從來沒有做過,那過去的行政部門也從來沒有面臨這些事情,所以相對而言是沒有經驗。那第二個問題是,他在國會上的少數的結構,就是民進黨在國會上是少數的結構,那它可能面臨一些阻礙,可能要去提倡這整個人權施政的時候,所面臨到行政部門的經驗不足,以及在立法部門可能是結構性的少數,可能相對而言有一些阻礙。不過它的正面是扮演了火車頭,開始讓火車啟動。那馬政府的部份的話,我是覺得它變成是說那個火車頭帶領的概念比較消失了,可是它的好處是,它在國會當中是多數的結構。也就是說它如果想要發動某些事情的時候,是有可能,有結果的。比如說:兩公約的批准的情況,可是問題點是說,它沒有...我覺得沒有把握好這個契機,如果它其實想要做的話,是可以扮演很多火車頭拉動的角色,可是卻沒有,去好好的去結構性的思考,這些基本的概念。但我個人主觀上是認為說,馬政府可能它的政治幕僚,政治幕僚沒有去注意到這個問題、這個問題。那畢竟人權諮詢委員會它是一個兼職的情況,它沒有辦法有比較穩定完整的有政治幕僚去做...講一句實話,去做政治的思考,跟安排。我在這個人權議題上面的話,應該是有哪些議題是必要做的、如何去做,這在安排什麼時間去做,這種比較結構性的思考。那所以說,你會發現我覺得馬政府相對而言反而是在有民間團體督促的情況之下、或者是提醒的情況之下,那些議題才去處理,而並不是扮演一個比較帶領的角色。這是我覺得相對而言比較可惜的部份,不然以整個執政架構來看的話,其實馬政府是可以扮演這種結構帶領、讓台灣的整個不管是人權法律、人權文化更加落實的一個可能性。
黃:那民間團體呢?你怎麼看?這兩個扁政府跟馬政府時代的民間的活動?民間團體的成長?民間團體的運作?你怎麼看?
廖:我個人參與比較多是台權會的工作,那我比較欽佩台權會...到目前為止是它的獨立性,作為人權團體的話,不管面對哪一個政府,它基本上維持他們獨立性的一個人權的訴求,這是我對台權會比較欽佩的部份。那相對而言我相信在民間團體不只是台權會,在面對兩個政府的時候,我覺得那個彼此的溝通的那個程度,以及互動的程度的話,我覺得還是有點差別。比如說?因為扁政府想要扮演火車(頭)的角色,所以說它提出了某些東西,這些東西勢必我覺得可能跟民間團體的互動性就比較高。那相對而言,你看扁政府時代的話,民間團體好像..我開玩笑動力好像變少了,所謂動力就是說,好像你對甚至好像對那些社運的部份被某些政府的...吸走,相對而言...(黃:對,有這樣的說法。),好像有點降低了。那到馬政府時代的時候,我覺得就是說,它後續跟民間團體,特別是人權團體的互動性恐怕是比較沒有那麼的充分,也就是說我所瞭解其實馬政府跟所謂的民間團體其實並不是直接的人權團體,互動性比較高,而是它所稱的社福團體,可能互動性比較高。那這部份我覺得互動那個訴求的強度是不一樣的,那所以說你會發現好像民間團體又轉過來對政府的批判性增加了,就增加了這個部份。
黃:我想對很多外國學者來看,台灣的民間組織是非常活躍的,非常有影響力量的。那比如說這次這個兩公約的報告,民間團體參與很多,你也參與很多,那這些我們邀來的學者專家都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說台灣的民間組織所能發揮的力量。那你看今後的情況怎麼樣?是不是這樣的一個民間團體的壯大成長?你的看法怎麼樣?應該是會再進一步的走下去?
廖:民間團體的話,我覺得它是有比較壯大跟成長,同時我覺得比較好的部份就是說,我們真正慢慢看到的台灣民間團體,真正叫做公民社會這種獨立自主的模式,我覺得是在台灣慢慢形成。但是我覺得在台灣的民間團體會有一個隱憂就是說,其實人力跟經濟的制約,其實是有相當大的壓力的。就是說人力資源你會發現,我們在某些團體的重疊性其實相當高;第二個它的經濟上的壓力,其實每一年都非常的重。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我們其實就很像大家所開玩笑,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其實台灣民間團體最可愛的也是人,因為有人的活力跟投入,那可是我覺得會有一些剛才我說的一些經濟上跟人力上的限制,變成會影響到民間團體它成長的那個...規模,這個規模。所以我是判斷,就是說我們在短時間裡面可能可以維持活力,可是卻沒辦法突破那個規模。那跟政府互動的部份的話,我不知道是幸運或是不幸啦,那黃老師你舉到的是兩公約審查的狀況。幸運的部份是說,政府似乎聽到了某一些民間團體的訴求,所以它安排了國際的獨立專家人選以及它的審查的流程是哪一些部份。可是我想說的是另一個部份,為什麼會發生這個狀況,其實它不幸的部份是、可能的原因是,我們的政府根本完全不瞭解,就是不瞭解這些本來應該怎麼做,但是還好就是說,因為民間團體的一些訴求或是建議等等,政府還有願意聽到,某一部份的意見把它納進去了。可是問題是,這不應該是一個長久的模式,也就是說他的這個模式的情況是、除非是民間團體盯住了每一個事項,然後訴求或者是很完整的內容、完整的方案,政府才會聽得懂,然後也才會去採納這些概念。那這樣子的話,那表示它、政府是不會成長的。那表示說在台灣,這整個行政措施,或是行政作為、法律的部份,我認為是沒有基礎的,也就是說它必須要成長到政府本身是有人權的概念,你不可能在任何的事情,好像就只是說要民間團體在提出這個...概念或方案,政府才能夠理解這些狀況,不然的話,我覺得未來是非常難預測的。
黃:OK,是,對,我想我們是不是就談到這裡?非常感謝廖福特教授的接受訪問,那這個假如我們回去再讀了你的這個訪談紀錄有什麼問題我們再回來問你,很謝謝、謝謝。
廖:我下學期還有開課。
黃: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