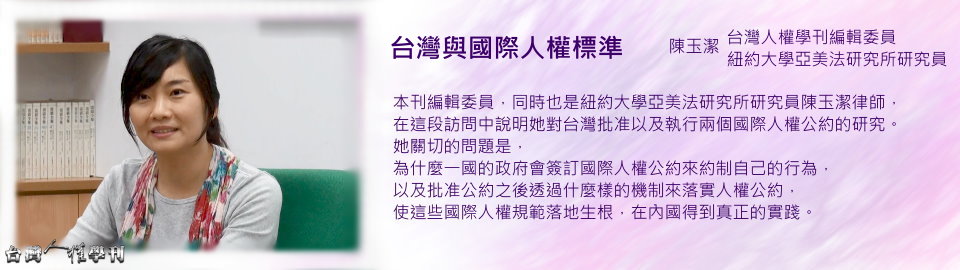
台灣與國際人權標準|專訪陳玉潔||人權群像第一季第四集
陳玉潔
本刊編輯委員,同時也是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陳玉潔律師,在這段訪問中說明她對台灣批准以及執行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的研究。她關切的問題是,為什麼一國的政府會簽訂國際人權公約來約制自己的行為,以及批准公約之後透過什麼樣的機制來落實人權公約,使這些國際人權規範落地生根,在內國得到真正的實踐。
黃:大家好,我叫黃默,是台灣人權學刊的主編。從去年開始,我們「試探」的這個系列的訪談,訪談了我們的編委,我們的作者,希望藉此使得我們的讀者進一步了解我們學刊的宗旨、我們學刊的活動關注哪些議題。那今天我們非常榮幸的有這樣的機會,玉潔律師,陳玉潔研究員,她這幾年來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不論是在事務上,還是在研究上,那待會兒我們再請她自己稍作介紹,當前她是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的研究員。那好些年來,是孔傑榮教授的研究團隊的一個非常出色的成員。那他們這些年來非常關注台灣的情況,台灣的法律、台灣的對人權的推動,同時也牽涉到中國大陸與台灣法律的比較研究。陳玉潔早年也在台北的「理律律師事務所」擔任過兩年的工作,所以她實務經驗非常豐富,在研究上又非常出色,所以我們非常榮幸地可以有這樣的可能性,來邀您來訪談。那是不是先請妳說一下妳的背景、妳研究關懷在哪裡、妳的活動大概都關切哪些議題。
陳:好,親愛的老師,我非常高興、很榮幸今天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那我先簡單介紹我的背景,我是在國內政治大學唸的法學士,也拿到了法律碩士,之後呢,就在律師事務所包括理律律師事務所,執業了前前後後有三年的時間,然後才到紐約大學唸法律碩士。那唸了之後我當時主攻的是國際法與國際人權法,那當時我就發現我對國際人權法相當地感興趣。所以後來就繼續在紐約大學伯恩斯坦獎學金的資助下,我就到了一個非營利組織組織「中國人權」工作,又在紐約工作了一年,之後才到紐約大學的亞美法研究所進行我的研究。那當時,決定要到亞美法研究所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其實是非常想要繼續學習研究台灣法律的制度,尤其是台灣的人權議題等等。所以我在亞美法研究所的研究主題還是不脫離我之前在紐約大學念書關注的主題,也就是國際人權法,還有其他刑事司法涉及人權的議題等等。那現在則是在紐約大學的法學院唸博士班。我其實在紐約大學博士班現在在寫的論文題目就是關於台灣在兩千零九年,批准了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的整個過程到它後續的執行過程,所以我關切研究的主題,其實是為什麼國家、一國的政府會決定要我們所說的TIED HANDS 自縛手腳去簽訂國際人權公約,來約制自己的行為。那再者就是在批准之後要怎麼樣去執行,把這些從國際引來的人權規範讓它可以落地生根,在內國真正的得到實踐,是透過怎麼樣子的機制去執行整個人權公約,這主要是我研究的主題。那這些我研究的主題,其實在國外已經有很多國際法、國際關係的學者在研究,那也有一些實證研究產生,我是希望說,台灣的這個研究,因為它是非常特殊的案例,也可以增加一些實證的資料,讓我們對於這些研究主題有更多的了解。
黃: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題目,在國內,沒有多少學者研究這個題目,可能大家都有些關心,但不是那麼明確的了解。那我想你的研究對我們來思考台灣的將來,台灣將來應該往哪裡去,我想應該是非常有幫助的。
陳:非常謝謝老師的鼓勵,我想沒有錯,這個領域因為是一個新興的議題,一直在兩千零九年之後,我們才慢慢注意到,國際人權規範可能對我們內國法制還有人權會造成一些影響,所以近年來是比較多學者投入他們的精力,在研究相關的議題,不過就我所知好像還沒有一個比較有系統性的研究,從這個批准一直到執行來做一個完整的紀錄跟分析。那我想我自己當初在設想說要研究這個題目的時候,我想遇到比較困難的地方是說在於研究方法。因為我想要做的是一個實證的研究,我其實對於法律怎麼樣規定,我認為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當我們把這樣的國際人權規範引進到國內的法制系統之後,它成為我們的法律的一部分,在實務上要怎麼樣得到實行,這才是我真正關切的主題。所以我當初在設想的時候,就是希望能用實證的研究方法。不過我覺得比較困難的地方,對我自己而言因為是學法律出身的,我並沒有社會科學的背景去從事這樣的實證研究,那那時候在紐約大學也修了些課,就發現原來我這樣的研究,是很適合用質化這樣的研究方法,包括訪談,去探知,不管是state actors或是non-state actors也好,他們對於國際人權規範,是抱持什麼樣子的態度,那他們當初會想要去接納國際人權規範,他們的動機又是什麼。以及就是在實務上,他們自己觀察到國際人權規範,在執行的結果影響又是什麼。
黃:那妳有哪些初步的發現?
陳:我想,因為我的研究論文有分兩個部分,一個是批准,另一個是執行。那批准的層面我比較關心的是,為什麼政府會去決定要批准人權公約,這個部分的發現蠻有趣的,就是在我們知道說其實當初在1990年末期的時候,剛開始是由民間的學者專家還有非政府團體,先去注意到我們台灣對於國際人權規範這個了解的缺乏,因此他們就比較有系統性的去介紹、引入國際人權去規範,那當時主要還是由黃文雄先生,他看到了他長年在海外,看到台灣其實一直從1971年之後就被孤立在聯合國之外,所以我們對於國際人權規範並不是那麼了解,那他看到了這個需要,當時就非常倡議的要把我們的人權規範,做一個跟國際比較完整的接軌。那當然黃默老師您也是推手之一,(黃:我沒有做什麼。)一直在做這個國家人權委員會,所以當時有一股助力,就是民間看到了我們台灣的需要,很可惜的是,當他們引進、試圖要介紹的整個過程,到陳水扁總統執政之後,雖然是有一股動力在推進,但很可惜就是,民進黨政府他當時並沒有成功批准這兩個公約,所以在陳水扁政府之下,我們看到有推動,但是沒有真正的、很多的結果。但我覺得他當時是種下了一個種子,到後來的馬英九政府上台之後,因為有了之前這樣的研究成果,加上馬英九總統他自己在執政之前,也提到人權議題,那麼執政之後,他也希望是以人權治國作為一個方針,那他在兩千零九年是成功地批准了。那我想我們從這當中可以看見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其實這個國家會去批准人權公約,他看的很有可能是有各方面的考量,那在國際上,他其實考量的是自己國際的地位,還有對於國家自己的認同,我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台灣他前面也提到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是因為我們退出了聯合國,可是其實也因為退出了聯合國,所以我們對於自己的國際地位,認知是比較敏感的,我們非常希望我們的國際人格可以被體認。所以在簽兩公約,當時很多的考量,是要去彰顯自己的一個國家主權的地位。再者就是,對於自己的認同,也就是說,我們在看台灣的時候,我們常常定位我們的論述上,都把它定位成一個民主的、尊重人權的國家。那麼在這個論述的過程,我們其實就把自己歸類成在世界各國當中是屬於民主陣營的,那這個論述也可以看到我們對中國大陸之間的比較,我們就會把它歸類成是另外一方,非民主陣營的。所以其實像這樣子的想法呢,在當初討論、批准也就是2003年陳水扁政府在討論批准的時候,是有很明顯的這樣子的表現。那所以在國際上,我們把自己看成是這樣一個國家,所以在用人權公約在彰顯自己的一個地位,跟自我的認知。在國內則是有政黨的競爭因素,因為陳水扁的民進黨政府他主張的是以人權立國,那時候其實應該是說非常的一個創舉,一個前面的政府從來沒有想過的,因為人權的議題雖然有提,但沒有把它作為一個主要施政的一個基本方針。那陳水扁他談到的人權立國,後來馬英九政府談到了人權治國,其實都是在做一個人權的競爭,那民進黨他其實是有一個優勢,因為他在執政的時候,在民眾的認知當中,他是屬於一個比較尊重人權,而且倡議民主的這樣一個政黨,所以他來做這樣的事情其實更有說服力,不像國民黨。所以當他開始做了之後,他其實是對他的政黨的形象跟論述,都是非常有幫助的,那在國民黨的時期,就不得不再來看看民進黨做了哪些事情,其中人權這一項目呢,我想已經被民眾拿來當做一個評分的標準之一了,所以國民黨也不得不做。所以有這樣的政黨競爭存在,總而言之,動機,要去批准人權公約的動機呢,是很多個層面的,從國際來看、從國內的角度來看,我想可以拼湊出一個比較完整的圖像。
黃:那我能不能進一步問那妳看現在批准的兩個公約也邀了國外的專家學者來審查,他們也提出了這個結論性的意見,是不是現在還是為時比較早一些,還非常難以判斷這一些政策,帶來怎麼樣的、對台灣人權的保障帶來了哪些實質的影響?我們不能做那麼明確的判斷,但是妳個人的看法,因為妳這麼多年來研究這個議題,妳個人的想像、妳個人的看法是怎樣?
陳:我想執行的過程,本來就是一個很漫長的、內化的過程,我一直覺得說我們要把國際的人權規範整個納入到我們的法律體制來,並且成為我們的社會價值的一部分,本來就會是一個很漫長的,內化需要時間,所以目前來講我們看到的,可能我想應該是比較表面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們,修改了一些法規,我們當然就是通過了兩公約的施行法,我們也做了國際人權的審查,我們也去檢視我們的法令,這一些至少在形式上是有做到,做得好不好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想說,目前我看起來,是我們確實有把這樣的機制納進來,那我一直想說,我用一個比喻喔,就是我們納入這個國際規範啊,在這些剛開始做這些機制還有審查會議,檢視法規這些過程就比較像是一個火箭的推進器,那這個火箭推進器,就是把這個火箭推上外太空之後呢,它就會脫離。為什麼我這樣說,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在做的這些事情,其實,都是,像國際專家來審查,它其實是一次性,以後我們會繼續做下去,但是,總是都是一次一次的,包括法規的檢視也是。你在剛開始,通過兩個公約的施行法之後,你做了一場的法規檢討,接下來應該也是要繼續做,但是這個後續做的動力呢,應該要從我們自己內部產生,我想國際專家沒有辦法長期的、然後非常頻繁的來檢視我們的人權的表現,那麼所以我就想說,其實這些國際的人權規範還有國際專家給我們的這些監督,比較像是一個推進器,讓我們的制度呢,能夠因為這樣子開始先有起步,那麼後面的就是要靠我們自己法制健全與否,然後還有我們政府機關有沒有願意認真去做這些人權義務的履行,我們的非政府機關能不能扮演好監督的角色等等。那,所以我們如果來看這個問題的話,我覺得要把時間拉得更長遠一點,現在我知道有很多非政府機關它其實不太滿意政府的表現,這個可以理解,因為政府目前來說它是還是走在非政府組織的後面,可是我覺得這個過程呢,如果說更長久的來看,我是比較有信心我們的台灣的法制環境其實是蠻健全的。那麼,從這個外界的監督一直到我們自己的法制的進步,我想是有辦法在未來看到國際人權規範給我們的帶來的影響。
黃:妳說得不錯,妳提到這兩個政黨的歷史背景跟對人權的立場,當前也有不少社會人士尤其是一些非政府組織,對馬英九政府有些質疑,尤其是看到馬英九政府希望進一步跟中國大陸發展比較密切的關係,不論是經貿關係,還是在文化上的交流,所以好些人就有些遲疑說這樣的情況,國民黨跟大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可能不可能影響到臺灣人權的進程?妳對這個問題做怎麼樣的看法?
陳:我想確實這個擔心我們在目前看到的很多議題上面,都非常的明顯,包括說這個媒體的過度集中、還有這個關於兩岸協議的這個民主監督等等,那我想這個是兩岸在未來要繼續發展和平共處的關係的時候,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那我想這個問題也不會只有馬英九政府會面對,未來的政府也會面對。我其實比較看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從另外的角度去出發,就是,我們會受中國大陸的影響,那我們自己要去想想,我們對於中國大陸能夠有什麼影響,那其實像這個批准兩個人權公約,我想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示範,那我們在紐約大學的亞美法研究所做這些研究的時候,也都一直強調當我們看台灣的法制進展的時候,我們其實就是提供了一個借鑒,因為其實兩岸的不管是歷史背景、同文同種的因素來看,我們有很多的經驗是已經走在前面了,而且這個經驗是值得他們參考的,當他們在思考自己的改革進展的時候,所以我在看這問題,例如我們簽訂批准了兩個人權公約,我反而希望我們的這個進程是可以提供給對岸一個、應該說是一個刺激,讓他們也可以去看看,如果說同屬中華文化的台灣,都可以做得到,那麼,也沒有說以這個亞洲價值作為藉口,而不去履行一些國際人權的義務的話,那麼中國大陸自然也就沒有這樣以文化的理由來說我們並不相信普世的價值。所以我想國際人權規範的引進,台灣應該要讓不管全世界,還有就是中國大陸那邊專家學者更能夠注意到台灣,它在這方面取得的進步。
黃:妳多年來也研究中國大陸的法律體制,妳到中國訪問多次,跟他們的學界也都有些互動,那我就想問那我們假設台灣的政策、台灣民間組織的活動、台灣社會的動向,對中國大陸有一個程度的影響,那我們有什麼樣的,因為妳在討論到研究方法的時候,提到實證的研究,我們在探討對中國大陸影響的時候,我們有多少實證的研究可以來比較進一步幫助我們釐清這個問題,就是說,是有影響的,也一步一步在發生影響?
陳:我想目前是還沒有這樣的實證去系統性的研究我們對於他們的影響是什麼,從我自己的觀察跟中國大陸那邊的學者這種不管是在會議上、或是非正式的交談上,我感覺他們對於我們台灣的經驗是非常有興趣的。當然有一些比較政治敏感的議題,他們不會去公開表示說台灣的經驗可以參考,但是他們都會很有興趣瞭解、研究。那從我跟他們的交流的過程中,他們甚至會要求我再寄給他們資料等等,因為他們想要去作跟自己的法制比較研究,所以我看到的是蠻令人鼓舞的這些發展。那我們自己去中國大陸開會的時候,我們在提倡說兩岸的這個專家學者或實務人士交流,我們也都會請台灣這邊的專家學者去說明台灣的狀況,那包括說台灣的法官、檢察官,那通常他們的發言,我們除了帶台灣的專家之外,也帶了美國的專家學者跟實務人士,那你就會看到說通常台灣學者、實務人士在發言的時候,中國大陸那邊、那一方的反應就非常的熱烈。兩相比較之下,就可以感覺出來,以比較法的使用程度,我相信他們對於台灣的感受是更為深刻的,尤其是在法制方面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議題。包括從威權時代遺留下來的一些破壞人權的這些問題處理。
黃:最後一個問題,這可能是一個大哉問,所以妳決定要怎麼樣來回答這個問題。那妳談到這個中國的傳統的文化,還是中國的這個傳承、同文同種,那妳看當代社會這麼樣急速地變遷,對這個、而且妳看台灣跟中國也在統治上、在統治的權力、在政府的體制、在經濟發展的模式、在生活的方式都有些不同的發展,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妳看中國傳統的文化的影響力量,是那麼樣的一成不變,我們可以假設是這個、對兩岸都有同樣的影響的力量,有同樣的接納程度,或是說經過這樣社會這麼快的變遷,台灣已經一步一步有了初步的、自主的想法,對中國文化、對中國傳統的價值,已經開始有些提出一些疑問,還是有些問題,妳對這個妳怎麼看?
陳:我想這是很好的、真的是很好的問題,也是很難回答的問題,那,我們確實兩岸在、尤其是在面對這些法制問題的時候,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相似性,但是也看到我們自己台灣對於這個法制的傳統價值,也跟著時代的進展有一些抗拒,那麼透過一些機制、法律機制來改革。那,我舉兩個例子好了,我想第一個例子很明顯,我們的、跟中國大陸有一點蠻不同的地方,是在於當我們在引進國際人權規範的時候,我們其實抱持著的是比較開放的態度,除了在少數的議題,例如說:死刑,這些比較敏感的議題上面之外,我覺得我們台灣對於這個國際普世價值的認同度這點是比較高的。尤其像我剛剛所講,我們在引進的時候,我們其實不太去談李光耀之前在談的亞洲價值,我們不認為我們跟歐美的民主國家,在尊重人權上面應該有什麼不同。我們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這樣子強烈的論述,所以可以看到如果說你要談這個有些傳統文化的影響,說我們可能對於西方那一套的價值不那麼能夠接受,我想這個在台灣,這一點上面你可以看到是跟中國大陸有比較大的不同。那所以我們在這一點上其實是我可以說覺得是比較去抗拒那種傳統文化說,因為傳統文化的關係,所以你的法制不能夠進展,這樣子的一些論點。我想這一點是比較不同,那麼我舉另一個例子,我想比較相同的,是剛剛提到的這個死刑議題,我想前兩天法務部開的檢討會議,裡面發現法務部提供的資料,還是去引述說我們過去的這個中國的傳統報應思想等等,所以我們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衍生出來這樣子的意思,這個觀念非常的根深蒂固,所以我們要保持這樣子的觀念。其實在這個保留死刑的論述上,如果你去看對岸的論述跟我們自己的論述,去發現有非常多類似的地方,而且主要這個立基點就是在於說我們傳統文化影響,我們不一樣。那其實我覺得這個可能也是誇大了,因為,在歐美各國他們對於這個死刑啊,你也可以發現,是民眾大部分在剛開始討論的時候,都是反對廢除死刑的,那麼他們的領導,有這樣的智慧跟有這樣的決心去推動,最後,廢除了死刑之後呢,民意有的有改變,有的改變比較緩慢,那麼,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是一個由上領導去帶領民意去教育民眾這樣子的過程。那我覺得說在台灣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政府有這樣子的決心,所以用這個傳統文化去做為一個沒有辦法做出改變這樣子的情況,我們還是看得到而且台灣跟中國大陸還是有相似性,我想這個現象是相當複雜,可能每一個、每一個議題我們必須分別來對待。
黃:我很同意,我想我們的時間已經到了,非常感謝妳接受訪問,妳上次到我們學校給我們的這個人權學程、人權碩士班,給我們講課,給大家印象非常深刻,非常有幫助,所以希望妳下次回來,再給我們講課,謝謝妳!
陳:謝謝老師!
相關連結:
到 卷
期
最新消息
- [招生訊息代轉] 114學年度東吳大學人權碩士班甄試入學報名資訊
- 台灣人權學刊更正啟示
- 台灣人權學刊更正啟示
- 台灣人權學刊更正啟示
- [活動訊息代轉] 2015人權國際交流研討會
- [活動訊息代轉]聯合國70週年論壇:聯合國與人權保障
- William Black教授與Ricardo Brodsky先生文章的英文原文已在本站發表
- [活動訊息代轉] 2014年東吳大學人權週活動
- [活動訊息代轉]蒙古的人權狀況-國際特赦組識蒙古分會秘書長阿爾塔女士座談會
- 「海外人權運動四十年」:王渝女士專訪。
- 在本刊發表文章中譯版的作者,現同意提供原文版本,在本刊官網發表
- 本刊第二卷第三期〈人權教育與世界公民:理論探討及其在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之應用〉一文漏列參考文獻,現已補正
- Nature Conservation in Taiwan
- [活動資訊轉發] 身心障礙人權與司法改革系列活動
- [工作坊資訊轉發] 2014 民間推動國家人權委員會 工作坊
- [活動資訊轉發] 三一八學運民主論壇
- [會議資訊轉發] CEDAW民間報告分享交流會議(全3場),歡迎報名參加。
- 台灣人權學刊網站全新改版
- 台灣人權學刊訂閱方式更新公告
- [研討會資訊轉發]「歐洲人權研討會」議程
- 人權不是錯覺!落實兩公約還沒有結論? 兩公約「結論性意見」之週年大考驗 暨 民間意見交流座談會
- 國際人權審查委員是朋友,不是敵人
- 為什麼台灣需要國際人權審查?
- 切莫錯失促進人權之良機 – 談國際審查
最新內容
- 第2卷第2期,2013年12月出刊
- 第2卷第1期,2013年06月出刊
- 中國民主運動研究|專訪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王興中兼任助理教授|人權群像第三季第七集(下)/張妙淨
- 中國民主運動研究|專訪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王興中兼任助理教授|人權群像第三季第七集(上)/張妙淨
- Professor Kar-Yen Leong’s Witness on Southeast Asia: Part 2|專訪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梁家恩副教授|人權群像第三季第三集|黃于哲/Yu-Zhe Huang
- 看見東南亞移工|專訪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張正負責人|人權群像第三季第六集/張妙淨
- Professor Kar-Yen Leong’s Witness on Southeast Asia: Part 1|專訪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梁家恩副教授|人權群像第三季第二集|黃于哲/Yu-Zhe Huang
- Professor Yu-Jie Chen’s Multifaceted Career: Researcher, Teacher, and Activist|Professor Yu-Jie Chen|人權群像第三季第一集|黃于哲/Yu-Zhe Huang
- Professor Seymour’s Reminiscence on Taiwan|James Dulles Seymour|人權群像第二季第七集|黃于哲/Huang Yu Zhe
- 推動台灣廢死最前線|專訪林欣怡執行長|人權群像第二季第六集/台灣人權學刊編輯組
- 台權會十年回顧|專訪台權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施逸翔|人權群像第二季第五集/台灣人權學刊編輯組
- 台灣人權教育現場|專訪湯梅英教授|人權群像第二季第四集/台灣人權學刊編輯組
- 學生權益與教師人權培育|林佳範|人權群像第二季第三集/台灣人權學刊編輯組
- 從友善校園到人權教育|專訪王秀津老師|人權群像第二季第二集/台灣人權學刊編輯組
- 從國際公約談人權議題及價值|專訪黃嵩立教授|人權群像第二季第一集/台灣人權學刊編輯組
- 學術研究與公共服務|專訪廖福特||人權群像第一季第八集/廖福特
- 理論與實踐的辯證|專訪顧玉玲|人權群像第一季第七集/顧玉玲
- 海外人權運動四十年|專訪王渝||人權群像第一季第六集/王渝
- 憲法與國際人權法的匯流|專訪張文貞教授|人權群像第一季第五集/張文貞教授
- 台灣與國際人權標準|專訪陳玉潔||人權群像第一季第四集/陳玉潔
- 台灣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應該設置在哪裡?|專訪魏千峯||人權群像第一季第三集/魏千峰
- 台灣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應該設置在哪裡?|專訪李念祖|人權群像第一季第二集/李念祖
- 她(他)們還是我們?|專訪陳文葳||人權群像第一季第一集/陳文葳
